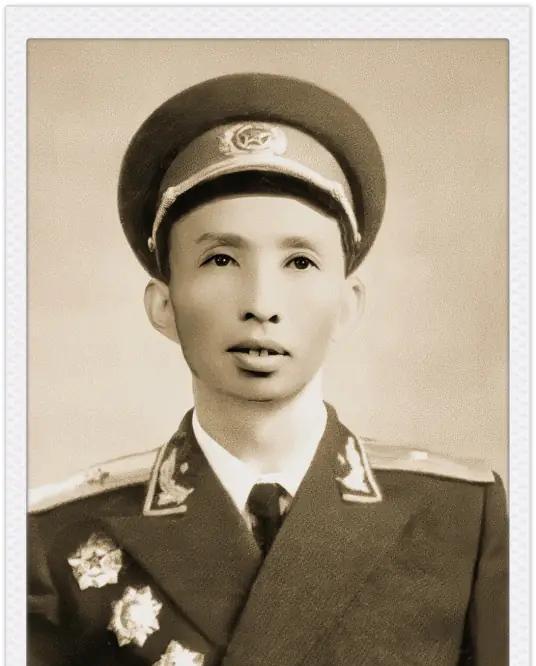国民党上将韩复榘被枪决后,他的妻子带着孩子颠沛流离,国民党战败后她带着孩子选择留在了大陆,而后她写信向国家申请要回自家的房子,得到的答复让她感动不已。 1952 年深秋,北京弓弦胡同的风卷着落叶,扑在高艺珍租来的小院门上。 她握着那支用了十几年的钢笔,在信纸上写下 “呈北京市人民政府” 几个字时,手微微发颤。 信里没提韩复榘的名字,只说 “民国年间在弓弦胡同有祖宅一处,现为公房,恳请归还以安家用”。 窗外,次子韩嗣燠正帮邻居修理自行车,叮当的敲击声里,藏着这个家庭最朴素的期盼。 这处宅院,是 1930 年韩复榘刚任山东省主席时买下的。那时他春风得意,在北平买下这处三进的四合院,给高艺珍和孩子们住。 长子韩嗣燮在这里启蒙,次子韩嗣燠在这里学会拉二胡,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,还是高艺珍亲手栽的。 1938 年韩复榘被枪决后,国民政府以 “逆产” 名义查封了宅院,高艺珍带着孩子逃离济南时,只来得及带走几件棉衣和孩子们的课本。 从 1938 到 1949,这十一年的逃亡路,高艺珍记不清换了多少地方。在河南漯河,日军飞机轰炸时,她把四个孩子压在身下,自己后背被弹片划伤。 在陕西西安,靠韩复榘老部下闻承烈接济的一千大洋,勉强租了间土房,冬天没煤烧,就和孩子们挤在一床被子里。 在香港九龙,为了给三子韩嗣烽治病,她变卖了韩复榘留下的最后一块怀表 —— 那是冯玉祥当年送他的,背面刻着 “同心报国”。 1945 年日本投降,她曾回北平找过这处宅院,那时国民党接收大员说 “韩复榘是战犯,房产充公了”。 她只能在胡同口徘徊,看着自家院门被贴上 “敌伪产业” 的封条,泪珠子掉在青石板上。 1949 年北平解放那天,韩嗣燠穿着解放军的军装回家,手里拿着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。 “妈,上面说‘凡属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财产,经查明确非贪污受贿所得者,应予保护’。” 高艺珍看着布告上的字,想起 1947 年在上海,国民党官员要她交出仅存的首饰 “支援戡乱”,两相一比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。 韩嗣燠那时已参加解放军,随部队南下作战,临行前对她说:“妈,留在大陆吧,新政府讲道理。” 她点了头,不是因为相信什么,而是累了,不想再逃了。 在北京安定下来后,高艺珍靠着给人缝补衣服维持生计。三子韩嗣烽在交通部门当学徒,小儿子韩嗣蟥在小学读书,长子韩嗣燮因父亲被枪决受了刺激,精神不太稳定,住进了疗养院。 日子清苦,可夜里能睡个安稳觉,不用再听枪炮声。只是每次路过弓弦胡同,她都忍不住多看几眼那座宅院。 那里有孩子们的童年,有她和韩复榘刚结婚时的样子,虽然那个人犯了错,可家总是家。 信寄出去后,高艺珍忐忑了二十天。她怕政府还记得韩复榘的旧账,怕那句 “战犯家属” 的帽子永远摘不掉。 直到那天,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找上门,手里拿着公函。 “高艺珍同志,” 为首的干部称呼她 “同志”,让她心里一暖,“经查,弓弦胡同宅院确为韩复榘私产,非贪污所得。 根据政策,予以发还。” 公函上还写着:“韩复榘历史问题已有定论,其家属按普通公民对待,享有合法权益。” 高艺珍接过公函,手指抚过 “合法权益” 四个字,突然哭了。这些年,她听够了 “汉奸老婆”“战犯家属” 的骂名。 在香港时连租房子都要被房东盘问,如今新政府不仅还了她房子,还称她 “同志”,承认她是 “普通公民”。 那天下午,她带着孩子们走进久违的宅院,海棠树还在,只是枝桠枯了一半。 韩嗣烽爬上梯子,把院子里的杂草清理干净;韩嗣蟥在墙角发现自己小时候埋的玻璃球,高兴地喊 “妈,你看”。 高艺珍坐在台阶上,看着这一切,觉得心里那块被多年委屈压着的石头,终于落了地。 后来,高艺珍在这处宅院里住到 1957 年去世。临终前,她拉着韩嗣燠的手说:“别忘了政府的好,好好干活。” 韩嗣燠后来在兰州电力技工学校当老师,一辈子兢兢业业;韩嗣烽成了交通部门的技术员,参与了多条公路的修建。 韩嗣蟥长大后留学奥地利,每次回国都要去弓弦胡同看看,说 “这里是根”。 那封答复公函,高艺珍一直压在箱底,上面的字迹虽已褪色,却像一道光,照亮了一个家庭在历史转折中的命运。 它让高艺珍明白,一个政权的温度,不在于如何对待胜利者,而在于如何对待失败者的家属 —— 不株连、不歧视,只论是非,只讲法理。